信息病毒,比新冠病毒传播得更快,更无孔不入,它不需要飞沫与接触,只需一个点击,一次转发,就能在数字世界里完成一场针对个体的“社会性谋杀”。
那个成都女孩的行程轨迹公布后,一场数字时代的“猎巫”行动旋即启动,她的私人生活被摊开在数亿用户面前,接受最严苛的审判,酒吧、串串香、美甲店……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场景,在键盘侠眼中变成了“不检点”的罪证,她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隐私信息被恶意曝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转场皇后”“毒王”等充满侮辱性的标签,一夜之间,她从一名需要关怀的普通患者,变成了全民公敌。

这种网络暴力背后,是根深蒂固的道德完美受害者迷思,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病人应该是无辜的、纯洁的,最好是在家与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良民”,一旦患者的行踪轨迹超出了这种狭隘的想象,就似乎失去了被同情的资格,这种思维将公共卫生事件异化为道德审判,将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扭曲为对个人私生活的窥探与评判。
更深层次看,网络暴民们通过谴责个体来宣泄对疫情不确定性的集体焦虑,当面对看不见的病毒和无法预测的传播链时,将责任归咎于一个具体的、似乎“有瑕疵”的个体,能够产生一种虚幻的控制感——仿佛只要谴责了这个人,病毒就不会威胁到自己,这种心理机制与古代社会遭遇天灾时寻找“替罪羊”的集体行为如出一辙,只是审判场从村庄广场转移到了网络空间。
在针对成都女孩的网络暴力中,还夹杂着不容忽视的性别偏见,一个年轻女性频繁出入娱乐场所,在许多人眼中天然地构成了道德瑕疵,如果换成男性,同样的行为可能只会被轻描淡写为“爱玩”,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社会中对女性行为根深蒂固的控制欲与规训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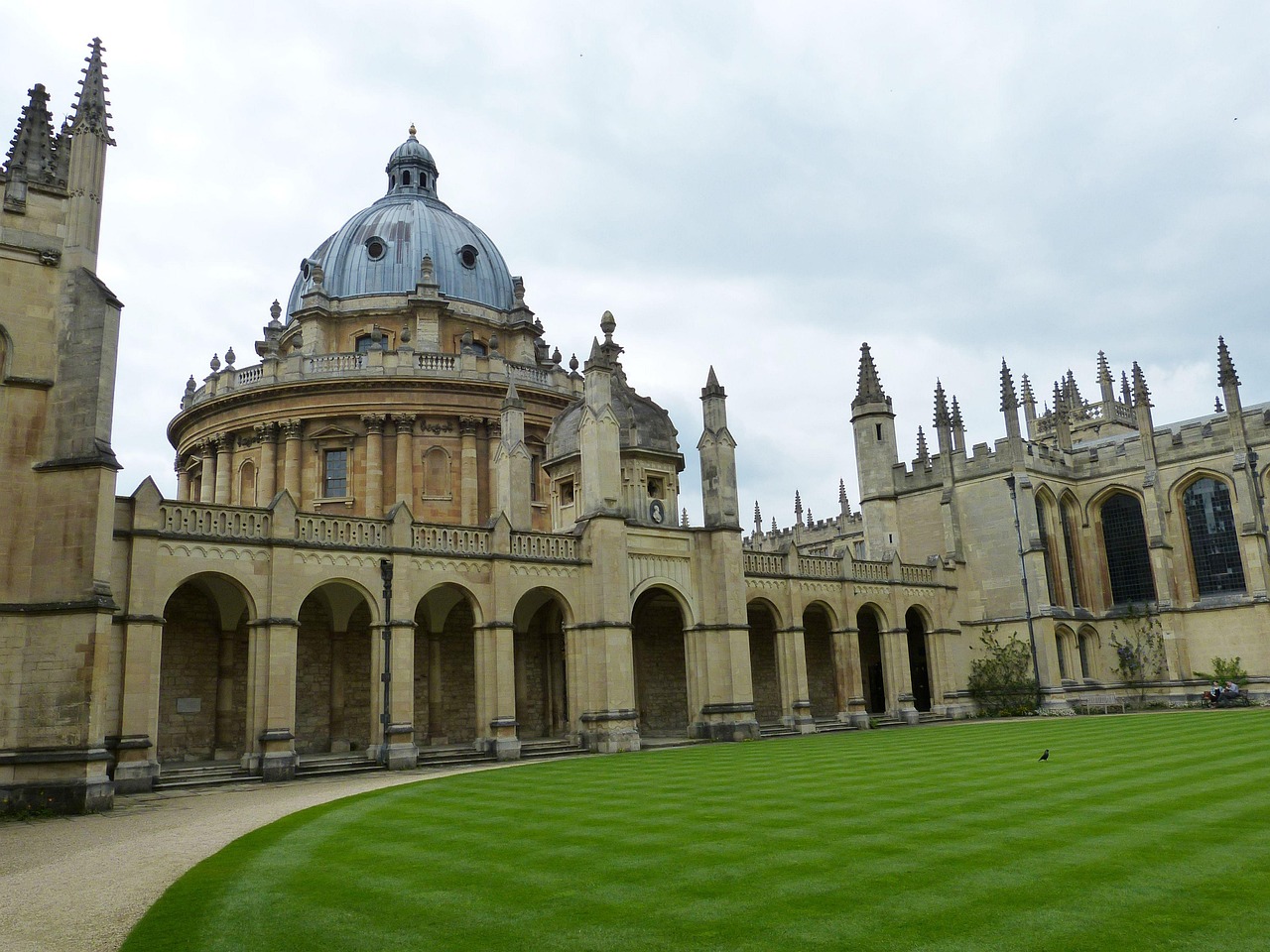
网络暴力的伤害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制度性的,当人们因害怕隐私曝光和社会性死亡而不敢如实报告行程时,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石就被动摇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安全都与整个社会的防疫成效息息相关,保护确诊者的隐私,不是对个人的特殊照顾,而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举措。
法律在遏制网络暴力方面展现出越来越明确的立场,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为网络行为划定了红线,那些自以为躲在屏幕后面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网暴者,终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二十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在制度纵容下,普通人也会成为恶的代言人,在网络暴力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平庸之恶的数字化变种:每个人可能只是打了一行字,点了一个赞,转发了一条评论,但这些微小的恶意汇聚起来,却能形成毁灭个体的洪流。
面对疫情,我们真正需要对抗的是病毒,而非彼此,成都确诊女孩的遭遇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尊重与善意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社会抵御危机的能力体现,当我们学会在标签之外看到具体的人,在愤怒之前保持理性的思考,我们才真正从这场疫情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希望通过本文,你能对如何看待成都确诊女孩遭网暴和如何看待成都确诊女孩事件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不妨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持续关注本站,解锁更多实用干货!"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