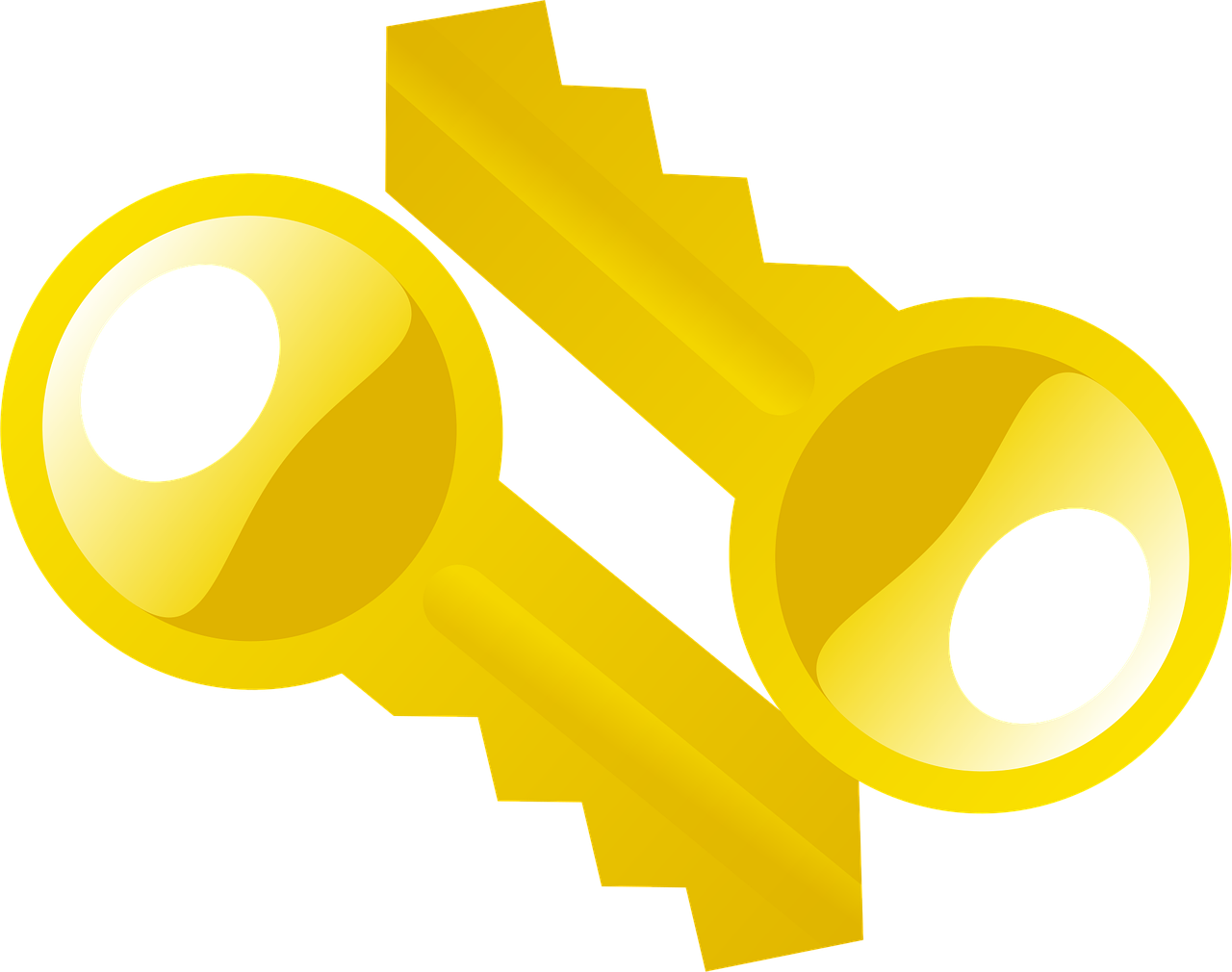在徐州东部的平原上,有一座小城静卧于黄河故道之畔,她有一个古老而富有诗意的名字——睢宁,睢者,水名;宁者,安宁,这个名字仿佛一道咒语,定格了这片土地的双重性格:既有奔流不息的活力,又有岁月沉淀的安宁,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睢宁如同一幅精致的双面绣,一面是千年古韵,一面是时代新风,在经纬交错间,绣出了一座小城的灵魂图谱。
古韵:黄河故道的记忆刻痕
睢宁的古,不是博物馆里被玻璃罩隔离的古,而是依然在呼吸、在生长的古。
清晨的岠山上,雾气还未散尽,我站在葛洪炼丹处遗址前,试图想象一千六百年前那位抱朴子在此采药炼丹的情景,山风掠过,仿佛还带着《肘后备急方》的药香,下山步入水月禅寺,这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的寺院,以“水中月,月中心”的独特建筑理念,将禅意具象化为空间语言,寺内不供佛像,却处处是佛心;不诵经文,却字字是禅机,同行的当地老人告诉我,抗战时期,这里曾是中共淮北党政军机关驻地,古寺见证了烽火连天,也庇护过革命火种。
这种历史的层累在睢宁博物馆变得更为具体,下邳古城沙盘前,我凝视着那座沉睡在黄河泥沙下的城市——它曾是徐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因康熙七年的那场大地震而沉入水底。“城头月,曾照下邳人家”,导游轻声念着不知名的诗句,在汉画像石展厅,那些粗犷有力的线条勾勒出汉代人的生活图景:宴饮、狩猎、农耕、战争... ... 石不语,却道尽了两千年前的烟火人间。
最令我动容的是白莲峪古驿道,走在被岁月磨得光滑的青石板上,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驿马的蹄声、商贩的叫卖、学子的吟诵、移民的叹息... ... 这条不起眼的古道,曾是连接南北的文化血管,输送着货物、思想和命运,一位正在路边晒玉米的老农笑着对我说:“这路啊,我走了七十年,李白可能也走过哩!”他那不经意的玩笑,却道出了睢宁人骨子里的历史感——历史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日常的背景。
新风:平原沃野的生机勃发
如果以为睢宁只有古韵,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片土地的活力,正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迸发。
在沙集镇的电商产业园,我见到了“农民电商”的奇迹,一栋栋崭新的厂房里,年轻的睢宁人正在电脑前处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具订单,谁能想到,这个不产木材的平原小镇,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家具生产基地之一?从最初的“穷则思变”到如今的“电商名城”,沙集模式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一位“80后”电商老板告诉我:“我爷爷那辈人种地,我父亲那辈人打工,我们这辈人在家里点点鼠标,就把生意做到了全国。”
这种创新精神同样体现在睢宁的儿童画上,被誉为“中国儿童画之乡”的睢宁,已有数万幅儿童画作品在国际上获奖,在睢宁儿童画中心,我看着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画作——色彩奔放,构图大胆,完全不拘泥于成人的艺术教条,一位小画家在画中描绘了她的家乡:传统的白墙黛瓦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比肩而立,古老的黄河故道边是飞驰的高铁... ... 这幅画仿佛是睢宁的隐喻——传统与现代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对话关系。

傍晚,我来到睢宁广场,这里正在举行“睢宁好人”颁奖活动,一位位普通却不平凡的睢宁人走上舞台:有坚守山村小学四十年的教师,有创办残疾人就业工厂的企业家,有义务照顾孤寡老人十几年的社区居民... ... 台下掌声如雷,许多观众眼含泪光,主持人的话至今回荡在我耳边:“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人间烟火。”
双面绣:在经纬交错间寻找平衡
离开睢宁的前夜,我登上县城的新地标——天成大厦顶层,俯瞰全城,一幅奇妙的图景展现在眼前: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青砖灰瓦,灯笼高挂;一边是灯火通明的现代商圈,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两者之间没有突兀的断裂,而是和谐共生,仿佛一曲用古老乐器演奏的现代乐章。

我突然明白,睢宁的魅力正在于此——她懂得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既不沉溺于过往的辉煌,也不盲目追逐崭新的潮流,她像一位智慧的绣娘,在时代的经纬中,绣出了属于自己的图案:经线是坚守,纬线是创新,在一次次交错中,完成了古韵与新风的完美融合。
回程路上,我想起睢宁朋友的话:“我们睢宁人啊,一只眼睛看着过去,一只眼睛看着未来,所以走得稳。”这话朴实,却道出了睢宁乃至整个中国无数小城的生存智慧——在巨变的时代里,既要接得住地气,又要看得见星辰。
黄河故道水悠悠,千年的流淌带走了泥沙,却沉淀了智慧,今天的睢宁,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以她的双面绣,向世界展示着一种可能:传统不是包袱,而是底气;现代不是断裂,而是延续,在这片充满张力的土地上,古韵与新风的对话还将继续,而每一次对话,都在为这座小城注入新的灵魂。
"希望通过本文,你能对徐州睢宁县和徐州睢宁县天气预报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不妨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持续关注本站,解锁更多实用干货!"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