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两根最为坚实的支柱,千百年来共同支撑着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准则。“孝”是向内的人伦基石,维系着家庭的稳定与温情;“义”是向外的道德担当,链接着社会的秩序与公理,二者看似一私一公,一内一外,却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在“役情”——这泛指一切需要集体抗争的重大灾疫与公共危机——的熔炉中,相互碰撞、融合、淬炼,迸发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孝义役情,不仅是个体在困境中的两难抉择,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在时代考验下的深刻映照。
传统的“孝”,其核心在于“顺”与“养”,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到无微不至的奉养与情感慰藉。《礼记》有云:“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在承平岁月,这体现为晨昏定省、膝下承欢,当“役情”突如其来,社会进入一种非常状态时,纯粹的、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孝”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古代,征役戍边,儿子告别高堂,奔赴疆场,是为“忠义”而舍“孝亲”;现代,疫情肆虐,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告别家人,逆行出征,同样是将对家庭的“小孝”暂时搁置,去践行对同胞、对国家的“大义”。
这种抉择,并非对“孝”的背叛,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孝”的内涵进行了拓展与升华,试想,若无人挺身而出阻遏疫情,任其蔓延,最终自己的父母家人又如何能独善其身?此时的“逆行”,表面上是“舍孝取义”,实质上是以“大义”之行,守护千万家庭的“小孝”之基,这是一种更为深沉、更具远见的“大孝”,古人云“移孝作忠”,在当代的“役情”背景下,便可理解为“移孝作义”,这份“义”,是对职业的恪守,是对社会的责任感,更是对生命至上原则的捍卫,当一位医生在电话里向年迈的父母哽咽道歉,转身却坚定地走入隔离病房时,他心中所承载的,正是这种经过淬炼的、融合了孝与义的复杂情感——对父母的愧疚与牵挂(孝),化作了救治更多生命的坚定与无畏(义)。
“役情”这场公共危机,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行孝”的形式,在物理隔离成为常态的日子里,许多子女无法亲身侍奉在父母身边,科技手段使得“远程关怀”成为可能,频繁的视频通话、线上购买的生活物资、不厌其烦的防疫知识叮嘱……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是在特殊环境下对“孝”的创造性表达,它告诉我们,“孝”的精髓在于“心”而非仅仅在于“形”,当社会需要保持距离以阻断病毒传播时,这种充满智慧的“云端尽孝”,恰恰体现了子女在遵守公共之“义”的前提下,对“孝”道的坚守与创新。
更为动人的是,在“役情”的宏大叙事下,“孝”与“义”的边界常常变得模糊而温暖,社区志愿者为隔离中的独居老人送去饭菜和药品,他们与老人非亲非故,此举是“义”;但他们在执行这份“义举”时,那一声声关切的问候、一次次耐心的帮助,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越了血缘的、社会大家庭意义上的“孝”呢?同样,子女在参与社会防疫志愿服务(行义)时,其行为本身也为家人树立了榜样,传递了责任与担当的价值观,这本身也是对家庭的一种精神反哺,是一种广义的“孝”。
回望历史长河,从古代的瘟疫、边患,到近代的战争、自然灾害,再到我们亲历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役情”始终是检验一个社会伦理成色的试金石。“孝义役情”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间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它要求我们,在和平时期,应悉心培育孝心与义感,使其根植于心;在危机时刻,则要有勇气和智慧,将小孝融入大义,以大义成全小孝。

归根结底,历经“役情”淬炼的“孝”与“义”,不再是两个孤立的道德标签,而是交织成一种更为坚韧、更具弹性的精神共同体,它让我们坚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挑战如何严峻,那份源自文化基因深处的、对家人的挚爱(孝)与对社会的担当(义),永远是我们在黑暗中穿行时最温暖、最明亮的精神火把,指引着我们穿越风雨,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便是“孝义役情”留给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启示。
"希望通过本文,你能对孝义役情和孝义疫情有更全面的认识。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不妨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持续关注本站,解锁更多实用干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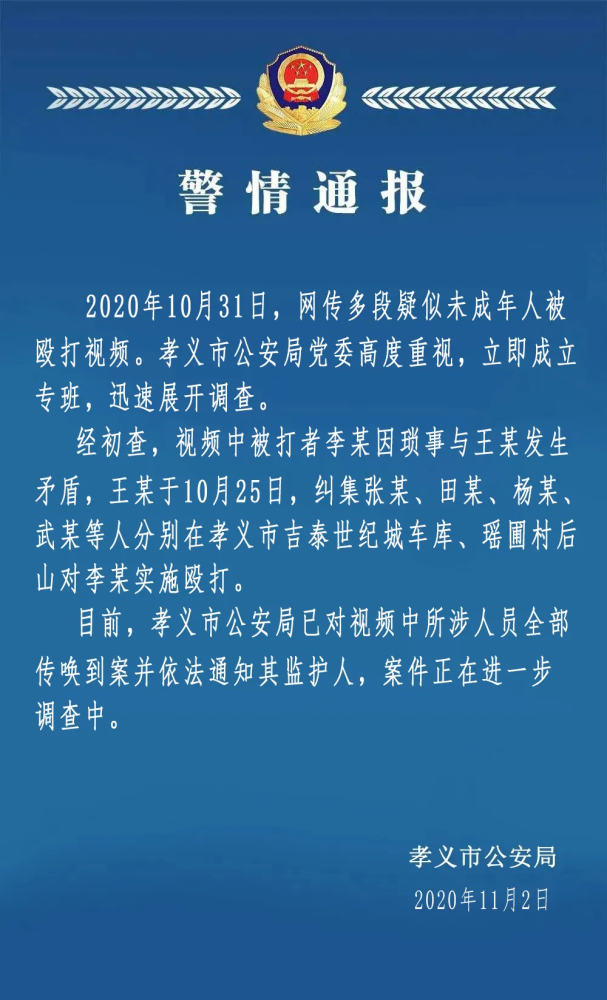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